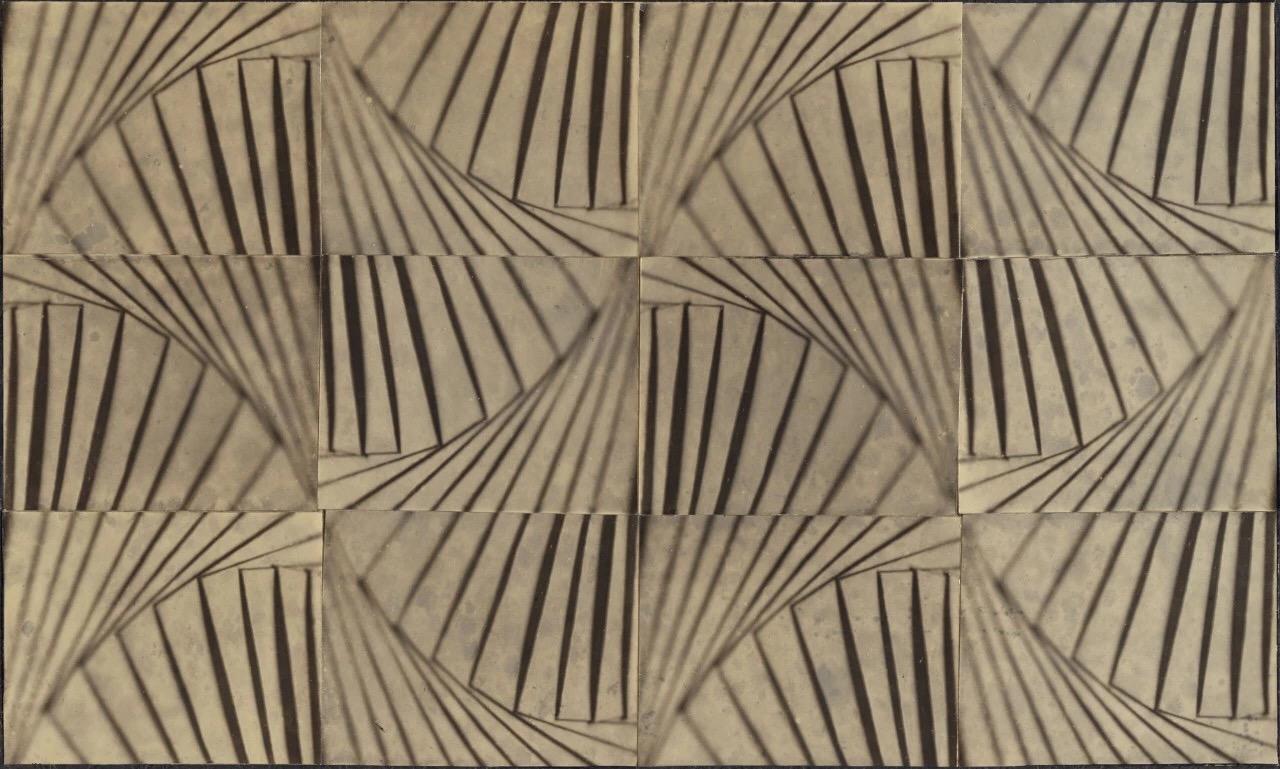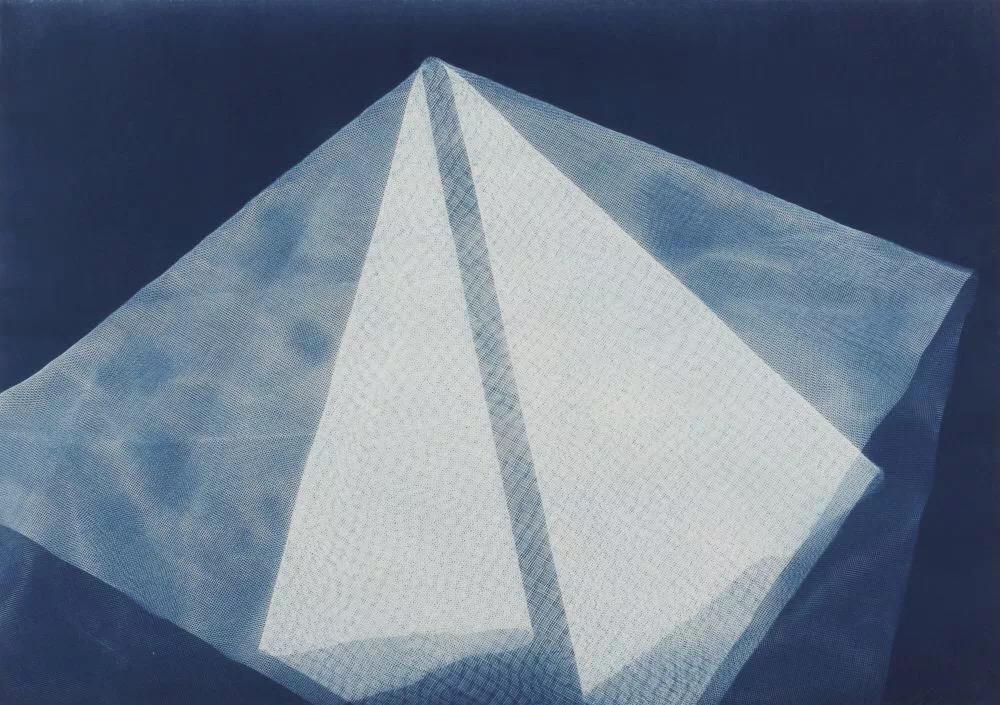Shape of Light: One Hundred Years of Photography and Abstract Art
在泰特看“光的形状”,聚焦摄影和抽象艺术交汇的百年
2018年9月24日
Art Newspaper Chinese 原始链接
在泰特看“光的形状”,聚焦摄影和抽象艺术交汇的百年
Tate Modern|泰特现代美术馆
London|伦敦
2018年9月24日Art Newspaper Chinese 原始链接